新闻中心
Our News
姑妈篮球的溯源④:女扮男装上朝鲜战场的姑妈

Our News
姑妈篮球的溯源④:女扮男装上朝鲜战场的姑妈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我在雷山县望丰乡任副乡长的时候,了解到在苗岭主峰雷公山深处的方祥乡提香村有一位女扮男装参加抗美援朝的叫王树才的老奶奶的故事。她从没有摸过篮球,却短短几年成为部队连队的篮球主力队员呢。
1950年的贵州省雷山县,是一个匪徒聚集的地方。1949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贵州后,继续向川滇康挺进。国民党残余势力看到人民解放军在贵州的部队不多,便纠散兵游勇、土豪劣绅等,组织土匪,对抗各级入民政权。1950年3月,保安第10团团长谢世钦把该团拉上了雷公山,组织起“贵州东南绥靖区司令部”,自封为司令,先后辖20个纵队,号称1.5万人,以雷公山为中心,派粮派款,抢掠烧杀,扰乱于周围各县。由于这股土匪的骚乱,黔东南的匪患愈演愈烈。为保卫人民政权,1950年8月,西南局从川西抽调第18兵团62军168师赴黔东南剿匪。9月15日,剿匪合围战斗开始。21日,节节胜利的168师向雷公山包围,采取梳篦压缩搜剿,做到山山有兵,村村有兵,道路设卡,渡口布哨,凡遇行人,细密盘查。
提香村,是雷山东部最边远的一个村,由于深居深山,几乎与外界隔绝,这个村既落后又贫穷,参加土匪的人不少。168师556团第2营5连的一个班驻进了王树才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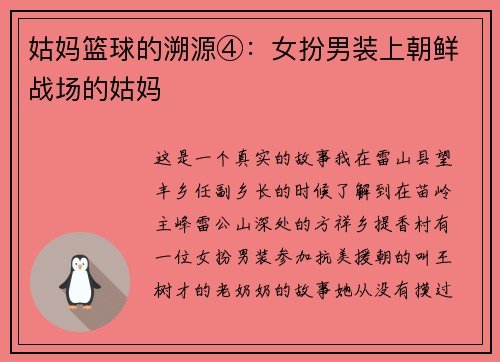
王树才的父亲是提香村的保长(现村主任),虽也与土匪有联系,但解放军驻进他家后,对他进行教育,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使他反过头来积极为解放军分析社情、民情、匪情。王树才的父亲是全村唯一见过大世面的人,也只有他会说汉话。年少的王树才经常跟随父亲到县城开会或赶集,因此也会说一些汉话。解放军正需要这么一个向导。班长就动员王树才参军:“树才,你懂汉话,你参加解放军吧。”于是,王树才参军了。然而班长万万没有想到,他眼前的这个一身男孩装年轻孩子,他动员参军的这个苗族战士,竟然是女扮男装。
她参了军后,就更不想让人知道自己是女儿身了,她怕身份一旦暴露,就不能在军队里呆下去了,她喜欢军队,喜欢当兵。
加入解放军后,王树才为556团带路歼匪,为清剿土匪的最后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1950 年10月15日,剿匪合围胜利结束。17日,王树才离开了家乡,到县城参加了万人庆功大会。王树才的命运,从此有了转变:风风雨雨、坎坎坷坷。
1950年10月8日,中共中央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毛泽东发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命令。10 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渡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北部,与朝鲜人民一起抗击美帝国侵略者。就在19日这一天,王树才被编进了雷山警卫营,任轻机枪班班长,担任清匪、镇反、保卫人民政权的任务。在雷山警卫营九个月,即至1951年6月,雷山县人民政府发出参军补充指示,经县进行严格体检审查,318名青年参加志愿军。王树才因在警卫营,表现又好,避免了体检工作,直接参加志愿军,开赴黄平,编入850团重机枪班。改编后入 856部(团)四连,成为17军50师成为一名野战军战士。王树才随军入朝时,已是1952年11月,美国和中国、朝鲜在谈判中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入朝前在沈阳已不再拿武器,而是把武器交沈阳入库后空手入朝,番号也去掉。
入朝后,王树才被编在志愿军铁道兵团3师13桥梁团1营,1952年5月,被改编到铁道工程第六师17团。1952年5月随铁道工程第六师参加宝成铁路建设。1952年年底,随铁道工程第六师赴朝鲜参战。在朝鲜参加抢修龟城至德川段宁边附近清川江畔任务和八院面至德川段铁路的独将峪段一条隧道等任务。部队住在离连部六里外的铁道干线周围的防空洞,任务是守护团管区最前沿的197大桥, 在美国飞机白天进行轰炸后夜间进行修复通车。抢修桥梁让自己部队的重要军列通过是铁道兵的一项重大任务,拖延通车时间,军列受阻即等于犯罪。朝鲜的冬天是漫长的,河里10月已结冰,6 月才解冻。战士们白天隐蔽,夜间抢修铁路和桥梁已是家常便饭。白天,美国佬的飞机一轰炸,夜间,你便会听到铁道上、桥梁上,劳动号子和铁器的碰撞声组成了一曲曲英雄混响曲。特别是在较高的桥上高空作业,又不能点灯,稍有不慎,就会粉身碎骨。一些战士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光荣牺牲了。王树才就这样和战士们一道,扛钢钎、十字镐、 八磅锤、木枕,一次一次完成了修复铁道通车、抢修大桥的任务。1953年3月,在一次抢修大桥过程中,气候突然恶化,地上本来已是冰天雪地,天上又落起大雪来,而且越下越大,只个把小时,本来已是一派雪景的大地更白了,把一个雪夜映得通亮。抢修过程中,王树才被换下桥休息,虽然冷,但王树才一下桥梁便躺在雪地上睡着了。这一躺,王树才便很难起来。王树才积劳成疾,病倒了。送到医院一检查,王树才患上了结核腰椎。而这时战友们才知道,整天和大家一起朝夕相处、同吃同住同战斗的王树才,竟然是个女同志。(这是我采访得到的个人陈述的信息,后有其战友的文章说,她是在朝鲜战争胜利回国后,1954年5月,王树才所在的志愿军铁道工程第六师17团在甘肃省天水市改编为“铁道兵第六师26团,继续修建宝成铁路。1954年9月,在调往广西修黎湛铁路时,王树才病倒住院了,才暴露了女儿身。)
王树才这一病,自然就不能在部队里呆下去了。她被送到广西桂林医院就医,后送湖南长沙陆军163医院住院,一住三年。治好病后,王树才被暂时安排在长沙陆军163医院消毒室工作。在工作期间,由于没文化,王树才在工作中吃了不少没文化的苦头。倔强的王树才没有被困难吓倒,她参加了文化学习小组。王树才是个活跃分子,她除了工作、学习外,还酷爱打篮球、射击。虽然个子矮小,但王树才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和吃苦硬拼的精神,而且她从小在家乡练就一身钻山爬树下水捉鱼的本领,学起球来很快,打起球来步法更是快似箭,身滑如鳅,成为女篮的主力队员,在长沙陆军163医院享有较高声誉。1958年,她被选送广州军区训练,到北京参加军人运动会,并被委任为运动会区副区长,负责40多名女军人运动员的训练生活。王树才参加篮球、手枪射击项目。1959年4月,王树才正式被安排在湖南长沙陆军163医院工作。在军区选拔赛中,王树才的手枪射击只获第八名,但在1959年5月解放军第二届体育运动会上,王树才异常发挥,竟夺得手枪射击第一名(可惜奖牌在“文革”中遗失),为广州军区立下了汗马功劳,也为自己的人生篇章谱写了亮丽的一页。
王树才被正式安排在医院工作后,她才开始与家里正式联系,然而,王树才信是写回家了,但却一直没有人给她回信。直到1963年,王树才父亲来了信,她才知道,父亲因为在民国时期曾当过13年的保长,已被定罪劳改13年,正在贵州省福泉劳改农场劳改。王树才父亲在信中说,他之所以一直没有给她回信,是怕连累到自己的女儿,这次非得来信,是迫于无奈,王树才父亲劳改的农场的驻地被烧,衣物全被烧光,希望王树才寄点钱给他购买衣物。而这封信,是组织上先看了信后才转给王树才看的。当时,王树才已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后鉴于王树才家庭历史不清白,组织上取消了其入党申请资格,同时还开除了王树才的工作籍。王树才的父亲没有想到,自己迫于无奈的一封信,就此毁了女儿的前程。
1963年10月,王树才回到了老家——提香。
医院开除了王树才,她并不因此而一蹶不振。她回到老家时,家里已空无一人。父亲劳改在狱中,母亲在父亲劳改后已病逝。大哥在王树才参军后婚育,有2男2女,但大哥大嫂在1961年困难时期一个因病而死,一个饥饿而死,留下4个遗孤给嫁在本寨的小妹抚养。回到家来的王树才依然是一身男人装束,寨子里依然无人道出她是女儿身。曾有媒人上门来劝说王树才娶媳妇,当时区里的一位姓宋的助理员也曾叫王树才去工作,因为有大哥的四个子女,王树才也就不再坦露自己的女儿身,谈婚论嫁,也不再去参加工作。她决定把大哥的四个子女抚养成人。
1964年5月的一天,王树才到方祥乡政府办事,路过方祥小学时,教室里传来的朗朗书声吸引了她。她在教室窗外驻足了半天,一个念头一闪即现,王树才决定,尽自己的所学所能,开办一所夜校。
提香村唯一能识些字的,便只有王树才的父亲和从长沙陆军医院学了点知识回来的王树才,不再有第三人能识字和会说汉话。从乡政府回家的当晚,王树才就到村大队长家商量办夜校的事。王树才的意见立即得到了大队长和大队委员们的支持。村里把上粮的一间小仓库 腾出来,就是学堂,学生有20多人。王树才白天参加村里的生产劳动,晚上就点上松油柴,给孩子们上课。没有一本书,全是王树才凭着自己在长沙陆军医院学的那点知识教;没有粉笔,王树才就和孩子们一起到村头白石坡去采一些白石头来做粉笔。王树才把部队里学到的军歌教给孩子们,从此,“雄纠纠,气昂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些革命歌曲响彻山寨。王树材办夜校的事传到了乡里和方祥小学,时任方祥小学校长的王佑强和教导主任杨通芳等人闻讯后赶到提香,让王树才开白天班,一个村办教学点由此诞生了。1964年9月,王树才开始了她的民办教师生涯。有了乡里的支持,有了书和粉笔,王树才办学的劲头更足了。她除了开办白班,夜校依然一如既往的开办,到夜校来参加学习的,都是大了一些的孩子和成人,每一夜教室里总是挤满了人。第一个学年度,王树才教的班级,竟获得全区一年级同级人均分第一名,区政府奖还给了提香小学一块黑板。
历史,总是给王树才的命运开玩笑。1985年第一次清退民办教师时,王树才第一批被清退了出去。孤独无援的王树才,又一次失去了工作,在村里当起了农民。
那时候,看着清瘦、苍老的王树才老人娓娓长谈自己的人生,我深深感到命运对她的不公。虽然如此,她依然没有一句对组织的报怨和不满。我最后按捺不住,请她谈谈有什么要求,我帮她去反映。王树才老人竟然说:你说在长沙陆军医院被开除的事,我能报怨组织么,那时对家庭历史不清白的人的处理都是一样的,我可以选择人生的道路,但我选择不了父母;1985年我被清退出民办教师行列,虽然有人从中作梗,但有一点我不能选择,因为我文化太低,再教下去只会误人子弟,我抱怨谁呢?现在我虽然老了,但我抚养的四个侄儿女已长大成人。还有,县民政局的领导们没有忘记我这把老骨头,每年都还发一些津贴给我,岁末年尾,还来慰问我,我享福呢,这一生,我不后悔。
我后来采访王树才的文章《苗岭深处“花木兰”》刊登在《当代贵州》(2001第七期)《贵州工人报》《黔东南日报》等报刊上。2002年初,《中央电视台》“讲述栏目”剧组电话联系我(那时是在永乐镇任党委副书记),说要到雷山来采访王树才老人,也一并采访我,邀请我一起到提香去。我于是把情况与县里作了汇报,准备好了去再度采访王树才老人的。谁知道在央视“讲述栏目”剧组就要启程的那天上午,方祥乡政府来电话说,叫我回话央视“讲述栏目”剧组,王树才老人在那个上午,与世长辞了(至于2005年王树才在铁道六师17团的战友梁文星,把王树才女扮男装抗美援朝事迹发表在2005年10月国防大学出版社的《血染金达莱》一书中,说“2004年王树才因腿摔骨折,卧床一年后于2005年病逝于家中”的情况,我是现在才看到这个说法,就没有去进一步论证了,因为我接的很多是当时的乡长打来的电话告知王树才去世的)。
很多年了,如今我依然记得,采访结束离开她老人家的时候,她与家人把送我们到村口。她拉着我们的手,含着泪唱着“感谢共产党”的酒歌与我们道别。走了很远很远,我们依然看见她依恋而挥别的手,依然听见回荡在山谷里的酒歌。
——谨以此文,纪念王树才老人,纪念和缅怀在抗美援朝中战斗与牺牲的英雄们。
(待续)